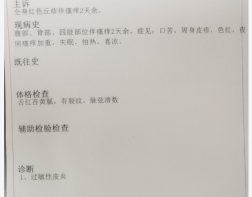书法知识
寻访古楼兰人后裔
点击量:577 时间:2022-01-12 04:34
提起楼兰,人们不仅就会想到神奇的罗布泊。罗布泊曾是我国第二大咸水湖,它位于新疆塔克拉玛于沙漠的东部,西起塔里木河下游,东至河西走廊,南邻阿尔金山,北到库鲁克山。我国古代史书上记载着,它曾是一个神话般的文明古国楼兰的所在地。
罗布泊历经岁月沧桑,到公元1975年夏天被太阳蒸干了最后一滴水。曾经烟波浩淼数千年,滋养了古楼兰文明的罗布泊,终于变成了茫茫沙海。
在罗布泊渐渐干枯的过程中,楼兰古国的臣民们相继搬迁到了哪里呢?他们今天生活的怎么样?
我虽然不是一名史学家,但作为一种对历史和事物的好奇,多年来我一直注意收集有关资料,曾经沿着史料的路径,多次到进入罗布泊荒原的吐鲁番盆地最南端的鄯善县迪坎尔乡迪坎尔村和南疆的尉犁县进行过寻访。
2008年7月初,我参加了吐鲁番地区作家协会组织的“关注楼兰最后一个村落――迪坎尔”活动,有机会再次近距离了解这个在地缘、民族、文化传承和血缘上与神秘消失了的楼兰古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的古老村落,以及生存在这个古老村落里的那些古朴、善良的与古楼兰人一脉相连的人们从罗布泊荒原迁途的故事和他们的现实生活。
走进盆地边缘的迪坎尔绿洲
七月流火。如果说吐鲁番盆地是“火洲”,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挟裹在著名的库木塔格沙漠和罗布泊荒漠之间的盆地边缘的迪坎尔绿洲就是名副其实的“火炉”。库木塔格沙漠由来至东天山七角井风口和西天山达坂城风口的两股强烈气流,所挟带的大量沙子在库木塔格山地相遇撞击沉积而形成,处在吐鲁番盆地最南端,而罗布泊荒漠则是众所周知的戈壁瀚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造就了迪坎尔绿洲“特殊”的神秘,以及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绿洲里的250多户“特殊”的村民。
迪坎尔绿洲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是一个被沙漠裹挟的村庄,柏油公路通到这里就停止了,一条连接文明与蛮荒的路也到此为止,绿洲也到此戛然而止,就好像这里已是大地的尽头、人类生存的边缘。它的东边是库木塔格沙漠铁色的沙山;向南是罗布泊无边瀚海;西边的流沙一年四季拍打着脆弱的绿洲;北边虽与绿洲相连,但可以看到流沙一直想把它撕开,使其成为一个孤岛,以图最终把它淹没。村庄就在公路的两边,村民的屋后就是库木塔格沙漠和罗布泊荒原的戈壁滩,无情的风把村民屋后的戈壁沙漠雕凿成一幅幅千奇百怪的巨型图案,迪坎尔绿洲则像戈壁沙海中的一个绿色孤岛、一叶泛舟……不管从村里的公路上穿过的是什么,也不管村里来了什么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庄依然保留着原始而古老的朴素,村民们依然保持着纯朴而随遇而安的祥和、安逸的似乎完全与他们生活的这片绿洲融为一体的生活方式。绿洲之所以世代枝繁叶茂、村民们之所以自由自在地繁衍生息,一切缘于村里那22条至今常年流淌的坎儿井和村民对水的珍惜、对生活的知足感。村民至今仍然沿袭着“先掏挖坎儿井,架起辘轳再成家”的习俗,姑娘嫁人首先要打听小伙子家附近有没有坎儿井和辘轳,吃水方不方便?小伙子要成家最要紧的是要学会掏挖坎儿井技术,否则会一辈子打光棍。难怪穿村而过的那条一年四季都清澈如镜的温泉坎儿井流淌的那么畅快(据说,温泉坎儿井冬季最冷时的温度在35摄氏度左右。)!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一架古老的木质辘轳,以至于迪坎尔村现在的一些自然村仍然以掏挖坎儿井的人和掏挖坎儿井的村子命名坎儿井,比如:米里克阿吉坎、牙克甫坎、纳瓦依坎(纳瓦依村)等等。
生活在迪坎尔村的村民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们与神秘的古楼兰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令人惊叹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生活追求。迪坎尔人对事物的理解有着他们自己的特殊方式,坎儿井是谁掏挖的就用谁的名字命名,哪个自然村什么东西出名、特殊就用什么命名,形成了现在一直在沿用的纳瓦依村(打馕人的村子)、其可其村(裁缝村)、牙克坎来苏(最边上的村庄)等自然村。迪坎尔村的很多人熟悉罗布泊就像熟悉自己家的院子和地里的葡萄瓜果、棉花和圈里的羊群一样,他们对罗布泊的地里环境和风沙、风向十分熟悉,村里的大多数人至今还经常到罗布泊荒漠里放牧羊群和骆驼。在这里,许多与现代文明看似格格不入、蒙着一层神秘面纱的现象,以及村民将古朴生活自然沿袭又自然而然地不断接纳现代生活的生存方式,一些偶尔遇见的黄头发、蓝眼睛村民和至今仍然居住在100多年以前用生土建造的土屋里而冰箱、彩电、甚至数字电视、电脑等现代生活品一应俱全的现实生活,让人的心灵不断受到强烈的抨击。更加令人惊叹的是,在这样一个边缘、荒凉的戈壁沙漠包裹下的村庄里,人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对学习汉话的热情、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尤其是对国家大事的了解和理解,如果不是身处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你很难想像到他们是生存在迪坎尔绿洲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的农民!
我大胆地设想:迪坎尔绿洲人们的这些“特殊”是不是古楼兰人血脉和生活习俗的延续?!
我们这些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走在热浪滚滚的迪坎尔村的村道上,走进百年古村那“冬暖夏凉”的生土建造的土屋,与始终面带纯朴的微笑、偶尔遇见的黄头发、蓝眼睛的村民搭话、聊天,吃住在他们的家里,与他们面对面接触、沟通,感受他们千百年来几乎一成不变的知足、安逸、和谐、纯朴而安然的生活。尽管从早到晚都有一种生活在“桑拿房”里的不适,但是,他们那近乎古朴的憨厚和友好,以及对我们这些外来人始终“不设防”的诚实和信任,还有那些老人和孩子善良、友好的眼神……这些始终令我的灵魂震颤、意识神游、飘逸、动荡的现实,使我有一种在楼兰古国里畅游的神往。
记得刚到迪坎尔那天晚上,由于天气实在太闷热,我和地区作家协会的刘秘书长,还有鄯善县文联的一名作家在“罗布泊向导”白克力·艾海提的安排下,住在他家屋后的迪坎尔烽火台宽大、平坦的台面上。在漫天繁星下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的烽火台上,我们三个人一边畅想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和罗布泊荒漠中古楼兰的美丽、繁华,以及楼兰美女的风姿卓韵、千娇百态,一边神侃千古奇闻、古今文人墨客对楼兰古国、楼兰美女的向往和赞叹。不知不觉中我们干掉了两瓶东北老酒,眼前的镜像顺着意境开始像梦游一样在自己的意识里游走、幻想……我对躺在我旁边的刘秘书长神侃眼前的幻影。仰望头顶正对的北斗七星勺把和数也数不清的繁星以及繁星下空旷的银灰色库木塔格沙漠在不远处的迪坎村道上穿梭的车灯折射下映射出的酷似古城墙的影像,不知道是潜意识的驱使还是大自然的神奇幻影,我告诉刘秘书长我看到了楼兰故城高高的城墙和城墙上楼兰美女的婀娜舞姿、城墙下热闹繁华的市井、车马……
尽管酒后夜宿迪坎尔烽火台我看到是一种自我意识神游的幻影,但是,黎明前站在迪坎尔烽火台上、站在库木塔格沙漠的沙山顶上,遥望远处库鲁克塔格山脉银灰色山峦起伏绵延周围的罗布泊荒漠的凄美和库木塔格沙漠与罗布泊荒漠之间的迪坎尔生机盎然的绿洲,我似乎感觉到自己终于触摸到了古楼兰人迁移的些许脉络,以及迪坎尔绿洲与楼兰古国的密切联系和迪坎尔人与楼兰人之间存在的神秘渊源。
探寻古楼兰人后裔迁途踪影
据史料记载,楼兰古国,原位于鄯善县南部的华夏第一县若羌县北、神秘的罗布泊以西、塔里木盆地东缘,迄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被中外学者誉为沙漠中的“博物馆”、“东方的庞贝城”。《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捍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四万四千一百。”
“地名搬家”是历史上地名常见的一种现象,一般同人口迁徙相联系,今天的“鄯善”县名就源自鄯善人的迁徙。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西汉王朝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派平乐监傅介子刺杀了位于塔里木盆地东缘亲匈奴的楼兰国国王,另立新王,并将楼兰国名改为鄯善。此后数百年间,鄯善一直是楼兰的国家名称。我们今天所说的楼兰,实际上是鄯善国的一座重要城市。当时这里是塔里木盆地重要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5~6世纪时鄯善国屡遭攻击,多次被灭,从而造成鄯善人口多次向外逃徙,相毗邻的高昌成了鄯善居民逃难避祸的场所。公元5世纪末,南齐使者江景玄受命出访西域,当他到达鄯善(楼兰)时,发现这个富庶的绿洲王国已经被丁零人消灭了,百姓们都已四处逃散,整座城池空无一人。此后的1500年间,再也没有听到过楼兰的消息,这个曾经声名远扬的古国如一阵风消失在浩瀚的沙漠戈壁里。1901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意外发现楼兰的消息轰动了世界。与此同时,诸多谜团也随之摆在人们面前:楼兰是怎么灭亡的?楼兰人是什么民族?其语言、文字、风俗又是怎样的?国家灭亡后,楼兰人去了哪里?
许多史料证实,最后的楼兰人后裔(罗布人)迁出罗布泊地区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60年代。也就是说,楼兰古国在公元三世纪神秘消失以后,楼兰古国的臣民们并没有全部逃散、迁走,他们固守在罗布泊,逐水而居,直至水一滴滴蒸发而迫使他们不得不继续迁徙。楼兰人的迁移时空跨度延续了大约1700多年,他们的主要迁往地有南疆地区的若羌、且末、尉犁和东疆地区的鄯善、哈密、伊吾,以及内地的青海、甘肃、西安、河南等地,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最后一批楼兰人的后裔才从罗布泊荒原的辛格尔迁到了今天鄯善县的迪坎尔村。
《魏书.鄯善传》、《宋书.索虏传》等史籍中记载:公元422年,鄯善王比龙世子率4000余国民归降北凉王沮渠安周,并随其迁居高昌。来到高昌后,这部分楼兰人被安置在库姆塔格沙漠北缘的绿洲地带,楼兰人将这片绿洲命名为“蒲昌”,以示对故乡罗布泊蒲昌海的纪念。至今,当地维吾尔族群众仍将鄯善称为“辟展”,即“蒲昌”。有关专家也认为,今天的鄯善县东巴扎故城遗址其实就是唐代的蒲昌城遗址。楼兰人向吐鲁番盆地的移民活动也被在火焰山下的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代文书所证实,这些文书中记载了大量关于“鄯”、“善”姓人名,考古学家根据西域人以国为氏的习惯,断定这些人都是楼兰国的移民。
走近迪坎尔绿洲古楼兰人后裔
古老的楼兰王国虽然消亡了,但它的臣民们在迁往新的栖生之地以后,在古老的罗布荒原周边的绿洲,又建立起了新的幸福、祥和的家园,创造了西域古老的历史文化、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楼兰文明也因此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延续。
约翰·海尔在他1998年出版的中文版《迷失的骆驼》一书中,详细记录了他深入罗布泊腹地探险、寻访野骆驼的经历。这个英国人在他的著作里清楚地记录下了最后迁移的楼兰人后裔,他们于20世纪60年代迁到了今天鄯善县的迪坎村。约翰·海尔在他的著作中记述了迪坎尔村的楼兰人后裔吐尔迪阿訇,他爷爷的哥哥阿不都热依木就是1901年与罗布人奥尔得克一起为斯文·赫定做向导的罗布泊猎人。斯文·赫定在《我的探险生涯》中描述:“在都拉里村北的一个树林里,我们巧遇从北面辛格尔来的阿不都热依木,他是整个沙漠中仅有的两三个知道‘六十个泉’的猎人之一……解决那个移动的罗布淖尔的问题,要经过沙漠没有一个起点比‘六十个泉’更稳妥,我决定雇佣他和他的骆驼。”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水,是罗布淖尔(罗布泊)的灵魂所在,没有了它,罗布淖尔(罗布泊)便成了没有生命气息的荒原。楼兰人,也是这样一点点散失了自己的家园,并且,永无返还的可能,最终使曾经在丝绸之路上十分辉煌的楼兰王国消失在罗布泊荒原中。
罗布人奥尔德克1934年又再次帮助另一个瑞典人贝格曼(有人说是斯文·赫定的助手)发现了罗布泊荒原中著名的小河(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小河墓地),发现一具保存完好的“楼兰美女”船形棺木,被其安祥的神情和完好的保存所震惊,称她为“楼兰公主”,但他无法带走她,只好就地掩埋。“楼兰美女”中有两个非常著名,一个是1980年发现的楼兰美女,那是在我国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楼兰科考时,于龙城雅丹南边一带发现的女干尸,当时轰动一时,这位楼兰美女生活于公元前3900年左右,有棕黄色的头发,皮肤呈红棕色,后来被新疆博物馆收藏。另一个是2004年小河遗址重新被发现后,在那里出土的一具女干尸,她比1980年的那具保存得更完整,并且更加年轻美丽。1980年的那具是壮年妇女,有40岁左右;而这具只有20多岁,身材更修长,长相也非常清楚,这具名副其实的楼兰美女被收藏在若羌博物馆。后来专家将两位楼兰美女头像复原,供更多的专家考证。通过躺在博物馆里“楼兰美女”和专家复原了楼兰美女画像,我们似乎觉得古人和今人的距离并不是那么遥远。
新疆青年诗人沈苇说:“奥尔德克既是出色的向导,更是沙漠里的预言家。一位土著居民不自觉地发现与职业探险家自觉地发现结合起来,才使我们对历史的挖掘、对文明的探寻成为可能。”。
奥尔德克的后人后来迁移到了罗布泊荒原的辛格尔居住,60年代初迁到了迪坎尔村。他的孙子白克力·艾海提如今成了著名的“罗布泊向导”,经常带领国内外的探险家出入罗布泊荒原,似乎在有意无意间巧妙地步入先辈的后尘。其实这是一种无法言表的血脉传承,所不同的只是时代和环境、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罢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人约翰·海尔和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专家袁国映教授、探险家赵子允一起,考察过面临灭绝的野骆驼的生存状况,之后写了著名的《迷失的骆驼》,书中有一张迪坎尔村吐尔迪阿訇的照片。去年8月中旬,我踏着流火的热浪,在迪坎尔村支部书记玉山·阿不都的引领下,找到了约翰·海尔在著作中提及的罗布人后裔吐尔迪阿訇的家。
吐尔迪阿訇现在的名字叫叶赫亚·沙依木。改名字的事情还有一段故事。被称为新疆“麦加”的吐峪沟清真寺依玛木觉得他原来的名字没有什么意义,于是在1986年春天的一天便给他改为现在的名字,意为“永远不老,健康长寿”。提起《迷失的骆驼》一书中关于他的一张照片,已经70多岁的叶赫亚·沙依木显得很兴奋,他说这是“骆驼子”(他对约翰·海尔的昵称)1997年春季来迪坎尔时照的,当时自己57岁。他告诉我,他们一家是1950年春天才从罗布泊荒漠的辛格尔迁到吐峪沟乡洋海村的,1956年又从洋海村搬到辛格尔生活了5年,1960年春天又迁到了当时水草丰茂的迪坎尔村。叶赫亚·沙依木说,他们一家在罗布泊荒漠的辛格尔生活了好几代人,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了。据老人们讲,从鲁克沁王时代他们就生活在辛格尔,因为那里水草茂盛,野生动物很多,是大家生活、狩猎的好地方。那时候居住在辛格尔的人有很多家,老辈人能够记住的大概有好几十家人,祖祖辈辈居住了有一百三四十年了,他自己是家族中的第四代,就出生在辛格尔。
老人肯定地说:“我的家族很久以前是生活在鄯善的,我家是鄯善人。”接着又他有补充说:“我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罗布淖尔(罗布泊)边上的鄯善。”
其实,老人所说的“鄯善”就是当年罗布泊荒原中的楼兰王国。约翰·海尔在《迷失的骆驼》一书中只写下了“可能是罗布人后裔”等文字,也许是因为他没有搞清楚“楼兰”、“罗布泊”、“鄯善”之间的关系的缘故。考古专家在鄯善县境内挖掘出土的文书中,陆续发现了近60个姓“鄯”和“善”的人,文书纪录了他们在鄯善生产、生活的历史,证实了最后一批楼兰人中的一部分人在这里驻足停留、生活,并最终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见到叶赫亚·沙依木老人,不得不提奥尔德克这个名字。叶赫亚·沙依木老人兴奋地说:“罗布人奥尔得克和我爷爷的哥哥阿不都热依木经常在罗布淖尔(罗布泊)打猎,以后他们一起给外国人管骆驼,做向导。”他说,奥尔德克的祖先也是老鄯善人(楼兰国人),也生活在罗布淖尔(罗布泊)。大概是1901年的四五月份,有几名外国人(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等人)找到奥尔德克,要找一批当地人给他们驮运物品,带他们进罗布淖尔(即罗布泊)测量(实际是探险考古)。奥尔德克从阿布达勒村赶到辛格尔找到我家,让我爷爷的哥哥阿不都热依木和他一同去。
至于叶赫亚·沙依木和迪坎尔绿洲的村民是什么时候从罗布泊迁到辛格尔,以后又为什么从辛格尔迁到了迪坎尔绿洲的?迪坎尔人的说话比较一致。老人和村里其他从辛格尔过来的村民介绍,大概是一百二十多年前,罗布淖尔(罗布泊)的水越来越少,住在那里的最后十几户人家都搬走了,有的搬到了且末,有的搬到了尉梨,有的搬到了其它地方,他的祖爷爷和另一家人搬到了距罗布淖尔(现在的罗布泊湖心)西北150多公里的辛格尔。因为辛格尔在库鲁克塔格山北,那里有辛格尔布拉克(辛格尔泉)、依尔托古什布拉克(依尔托古什泉)等六十六个大大小小的泉,还有碧绿的草场、肥沃的土质。在辛格尔,他们生活了大概四代人。大概到了60年代初,新疆马兰基地部队进驻罗布泊周围,国家搞原子弹实验,辛格尔人就陆续整体搬迁了出来。叶赫亚·沙依木家和他家住在一起的另一家搬到了尉梨县的一个偏远的地方,后来又搬到了尉梨县附近的胡杨林(现在的尉犁县罗布人村寨风景区附近)。叶赫亚·沙依木一家搬到了现住的迪坎尔村。由于叶赫亚·沙依木的父亲认为他们是鄯善人,鄯善都迁到吐鲁番的辟展了,他们也应该去鄯善,所以父亲带着他和弟弟迁到了今天的迪坎尔村。叶赫亚·沙依木告诉我,他们在这里一直生活的很好,很幸福。
别看只有50多岁的玉山·阿不都其貌不扬,平时不善言谈,可他已经在迪坎尔村当了14年的村支书了。他介绍说,迪坎尔村现在全是土生土长的维吾尔族人,很多人都是从外地迁来的。由于各种原因,从罗布泊荒原的辛格尔搬迁到迪坎尔村的人家到底有多少很难说清楚,现在能够有记忆的大概也就几户人家,比较出名一些的也就是叶赫亚·沙依木一家和艾海提·米里克一家。因为,叶赫亚·沙依木爷爷的哥哥阿不都热依木曾经带外国人(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等人)发现了罗布泊里的楼兰古城遗址,以后经常有外国人和许多专家、旅游的人,还有新闻记者等来找他们家了解情况,名气比较大一些。艾海提·米里克父亲的哥哥就是和叶赫亚·沙依木爷爷的哥哥阿不都热依木带领外国人发现古楼兰遗址的阿不都米力克·奥尔德克,不过很少有人提起过,因为时间太长了,很多事情没有人能够记得那么清楚,他们家出名是因为他的儿子白克力·艾海提。提到白克力·艾海提,玉山·阿不都书记眼睛里充满了神采,他说:“白克力这个人是迪坎尔村现在很有威望的人,他经常带领外国人去罗布泊,继承了祖辈的血脉。艾海提·米里克一家是60年代初才从辛格尔搬迁到迪坎尔村的,可能是最晚从辛格尔搬迁来的。”。我问他:“你们的祖辈人是不是也是从罗布泊的辛格尔搬迁来的?”他憨厚地笑着说:“搞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们家是多年以前从鲁克沁搬到迪坎尔村的。”
其实,与从辛格尔搬迁到迪坎尔村的其他人家一样,无论是叶赫亚·沙依木一家也好,还是艾海提·米里克一家也好,他们在辛格尔都过着半耕半牧的生活。叶赫亚·沙依木一家当时种有10亩地,主要收获的是麦子、大豆、甜瓜等,还养了二三十只羊,冬季就到罗布泊去打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这使我想起了清代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罗布泊人不食五谷、不牧牲畜,以小舟捕鱼为食。”的说法似乎有很大的出入。其实有关专家认为,罗布泊人比印第安人更完整地保留了原始生活方式,几千年前的卡盆(独木舟)和烤鱼的柽柳枝,如今被他们的后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们仍然饶有兴致地使用着。在沙漠里,他们辨别方向的能力胜过罗盘。
叶赫亚·沙依木的母亲、姐姐都去世安葬在了辛格尔,搬迁到迪坎尔村时,他家只有他和父亲、弟弟三个人了。每次想到这段经历时,叶赫亚·沙依木老人都显得有些伤感和沉重。
玉山·阿不都书记领着我去艾海提·米里克家时,已经80多岁的老人坐在木炕上,脸上总是洋溢着慈善、和蔼的笑容,说话、记忆都有一些障碍,无法沟通。老人的孙媳妇告诉我,他的儿子白克力·米里克带领一个探险队去罗布泊了,大概三天以后才能回来。玉山·阿不都书记看到我在夏日酷暑下的失望表情,告诉我,迪坎尔村有一位116岁的老人买合托木汗·吾塔力甫,她是见证栖息在迪坎尔的古楼兰人后裔生活和迪坎尔历史的“活化石”,只是年龄太大,许多事情已经记不清楚了。我知道,迪坎尔村人的生存环境并不好,但村子里长寿的老人却很多。在我的执意要求下,玉山·阿不都书记带我见到了这位老人。老人虽然年事已高,而且无法与人交流,但是看得出身体状况比较好,据家里人讲,她一天三顿饭一直都很正常,而且半年前还能下地走路。在我和她的大儿子司马义·甫拉提简短的交谈交谈过程中,老人一直在用“菩萨”一样的眼神和我们交流着,这让我心中生出一些敬仰和敬畏,好像老人的眼睛能够看穿你的灵魂一样。老人五世同堂,有子孙30多人,她一生养育了15个子女,成活了5个,老大(实际为老三)司马义·甫拉提已经75岁了,身体比较硬朗。据司马义·甫拉提老人和老伴、儿子介绍,他们一家50年代从辛格尔搬迁到尉犁,在那里生活了5年多。因为辛格尔有几十亩地和几十只羊,父亲一直在那里,所以,60年代又搬迁到了辛格尔。以后由于部队在辛格尔驻扎,一家人和邻居一起搬迁到了鄯善县的吐峪沟洋海,一直到60年度末才搬迁到迪坎尔村的。遗憾的是,买合托木汗·吾塔力甫老人2008年4月份不幸仙逝了。7月份再次见到迪坎尔村支部书记玉山·阿不都时,他告诉我,迪坎尔村以前的4位百岁老人都相继去世了,现在村里9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7个。
迪坎尔人与南疆尉犁、若羌,甚至北疆的吉木萨等地一直有着通婚的历史。百岁老人买合托木汗·吾塔力甫娘家就是尉犁人,她的儿子司马义·甫拉提的老伴和儿子、孙子媳妇都是尉犁人,可以看出,他们与尉犁有着很深的血脉联系。
事隔一年以后我再次见到老支书玉山·阿不都时,他还是满脸挂着友善的笑,把外面径直领到了“罗布泊向导”白克力·米里克刚刚盖好的红砖房里,安排我们吃住在他家里。
一见到高大魁梧、一脸憨厚中透露着刚毅的白克力·米里克,我放开目光肆意地在他身上搜寻他的父辈烙下的罗布人或者楼兰人的影子,直到他憨厚地笑着用流利的汉话和我交谈。我说:“很多年以前就知道你了,去年夏天我专门找过你。”他像老朋友一样憨笑着说:“看来我们是有缘人,因为有缘人总会见到的。”。他那憨厚的笑和不怯生的友善也许是因为见多识广练就的,但他从骨子里流露出来的那种友善和憨态,似乎与迪坎尔村的村民如出一辙。
白克力这个名字我还是从北京画院陈雅丹写的文章中和一些断断续续的网络上了解的。其实,人们称白克力是罗布泊“活地图”并不为过,因为,迄今为止,他已经带领300多人进出罗布荒原三十多次。
罗布泊的神秘诱惑着勇敢者,不仅是探险家考古学者的天堂,也日趋成为探险越野爱好者的神往之地,但同时罗布荒原的险恶地形又使太多的人望而却步,若无向导带路,无越野交通工具,无充分的给养,进入罗布荒原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迪坎尔村许多村民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外探险家和考古学者的向导。也许是因为有着正宗罗布人血统的原因,白克力成了村里最有名望的向导。白克力虽然出生在罗布泊荒原的辛格尔,从小也知道人们说的罗布泊荒原中的六十六个泉,但他对罗布泊并没有什么概念,他不太清楚那么多人经常冒险进入罗布泊去做什么,但探险队员们谈起罗布泊时的兴奋和神秘激起了他的好奇。直到2001年8月29日,已故新疆探险家赵子允再一次带队进罗布泊的时候,白克力终于试探着向赵子允提出,想跟考察队进一次罗布泊,看看他们在罗布泊究竟做什么。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已故的新疆探险家赵子允经常带队进入罗布泊考察,每一次出发前和回来后,几乎都在白克力家落脚吃住。这是因为白克力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精通汉语的维吾尔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白克力的爷爷阿不都米力克·奥尔德克和他爷爷的哥哥阿不都热依木曾给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带过路,算是“名人”之后,那些寻踪觅古的人们,对这个颇感兴趣。
白克力·米里克是名副其实的罗布人后裔,家族中共有四代人曾经住在罗布荒原的辛格尔,他们在那里种地、放牧、打猎。现在,先辈的麻扎(墓地)还在那里。后来,爷爷那代弟兄4人中,两家迁到了南疆的尉犁县,两家迁到了现在的迪坎尔村。出于故土难离和对祖先崇拜的情结,白克力的爸爸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每年的春天都带着他,赶着毛驴车,经过3天的长途跋涉,到先辈的拱巴斯(祖坟)朝拜一次。累了,他们就原地休息,在周围转转。渐渐地,他对那里的地形就比较熟悉了,更主要的是他的父亲曾经神秘地告诉了罗布泊六十六个泉的位置。掌握了这个天大的秘密,白克力罗布泊里的一匹“野骆驼”,他曾经开着东风车敢带着乌鲁木齐16名探险人员乘坐一辆轿子车进入罗布泊。那是他第一次带探险人员,经历了6天6夜的生死磨难,最后把全部人员安全带出了罗布泊荒漠。事后他后怕了好长时间,也遭到父亲的严厉批评,很长时间不让他进入罗布泊。赵子允那次带白克力参加探险队事先征得了他父亲艾海提·米里克的同意。白克力负责帮探险队员做饭,沿途哪里有泉水和植物,他都十分熟悉,给赵子允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多次带他去罗布泊当向导。之后,白克力开始了他的职业向导生涯。2003年,白克力为广州游客王灿等七八个人带路,因不适应罗布泊多变的气候和不规律的饮食,王灿患上了肠胃炎,又拉又吐,面色苍白,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一路上,白克力不离左右,问寒问暖,搀扶他上下车,为他打饭。王灿非常感动,走到敦煌时,硬是塞给他1000元作为酬金。白克力用生硬的汉话说:“朋友的事情,还要计较钱不钱的吗?”王灿说:“钱不收吗,朋友不认了!”白克力只得收下。如今,每年的春节,白克力都要把自家产的葡萄干和红枣寄往广州。王灿还专门邀请白克力到广州等地去过,使他打开眼界,更加坚定了自己当罗布泊向导的信心。
“看,这是美国朋友寄来的。”白克力有点炫耀地拿出一个黑色檀香木做的上面雕刻着“华藏山社”和白克力名字的小牌牌和一张他女儿和儿子的照片展示给我们。看到我们分享他的快乐,他又进入房间换上一件印有“华藏山社”字样的黑色体恤衫和一摞照片展示给我们。他特意翻出一张有陈雅丹的照片自豪地对我们讲:“这个,陈宗器的女儿陈雅丹。陈宗器知道吗?他是科学家呢,他以前和斯文·赫定一起进楼兰探险考古。陈雅丹进了罗布泊好几次,都是我带的路,她在罗布泊湖心立的纪念她父亲的碑还是我帮忙立的呢。”他指着照片上的碑给我们看。
白克力不但是一个勇敢而又细心的罗布泊向导和迪坎尔村民羡慕的好人,而且还是一位十分有经济头脑的“商人”。他自己掏一万多元在罗布泊湖心立了三个石碑,分别纪念已故的余纯顺、赵子允和美国探险家朋友,目的是吸引更多的探险家和游人去罗布泊。
看到白克力十分开心地、不厌其烦地拿出照片和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物件向感兴趣的人们介绍,我便在一旁不停地按动快门,记录下这个罗布人后裔今天幸福生活的精彩瞬间。
迪坎尔绿洲古楼兰后裔的幸福生活
公元四世纪起,关于楼兰古国的记载突然从历史消失,不再现于任何史书。它消失的原因,一直是近代中外考古探险家孜孜探寻的谜,以至于对古楼兰人的去向众说纷纭。
历史毕竟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真相。我认为,既然是历史就需要有人书写,而书写历史、挖掘历史的人则是有心者和对历史、对生活虔诚的人。吐鲁番地区作家协会组织当地部分自治区级作家协会会员和对历史、文化、文学有一定兴趣的作者,在流火的七月深入吐鲁番盆地最南端的迪坎尔村,通过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和对他们生存环境的亲身感受,探寻古楼兰人后裔的迁途和他们今天的现实生活状况,这无疑是续写今天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迪坎尔古楼兰人后裔历史的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
今天的人们知道,罕见的蒸发量和几乎为零的降水量,使罗布泊成为真正的“死亡之海”,著名的旅行家,人称当代徐霞客的余纯顺,著名科学家彭加木都魂断这里。然而岁月如烟云散去,万古沧桑却留遗痕,人们共同的感受是:绝域罗布泊,依然充满荒凉可怖,凶险神秘。楼兰古国尽管离我们已经远去2000多年,留给我们的仅仅是一个遥远的神秘背影,然而,苍天有眼,他的臣民们却凭着顽强的生命力,一代代沿着历史的轨道向我们走来,通过寻访和史料佐证,古楼兰人的后裔们(古鄯善人)依然和今天的鄯善紧密联系在一起,难怪清光绪28年(1902年)辟展建县时定名“鄯善”,这说明当时的清王朝官员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有一部分古楼兰人(古鄯善人)的后裔逐水草而居,早已翻过库鲁塔格山北迁到了今日的鄯善。
我想,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一味地去探讨、考证一些历史史料的准确性,而应该把目光放在现在依然生活在罗布泊和库木塔格沙漠之间的迪坎尔绿洲的这些古楼兰人后裔的现实生活上,续写古楼兰人新的历史篇章,让更多的人了解古楼兰人后裔在现代社会中不再逐水草而居的幸福生活。
对于迪坎尔村我并不陌生,对于迪坎尔村今天的巨大变化我由衷感到欣慰!
1992年的冬天,我曾经采访住村的鄯善县工作队时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和柏油路,村民过着近乎原始的生活,日常生活基本采取的是“易货交易”,也就是说以东西换自己需要的东西,就连吃的盐巴也是赶着毛驴车从罗布泊的盐山拉运,自给自足,过着清静而与世隔绝的封闭生活。村里的老辈人讲,整个村庄几乎没有一个人去过只有80多公里的鄯善县巴扎(集市),更不用说100多公里的吐鲁番了,唯一见识过巴扎的是村里的老阿訇。那是新疆解放以后的一年春季,听说鲁克沁王居住的地方成了穷人随便走动的地方,村民便请求老阿訇代表全村人去见识一下。我记得在鄯善县当过县委书记的岳立仁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改革开放初期,吐鲁番地区一个文工团来到迪坎尔村有偿演出,没有演出场地,一时难住了工作人员。正在大家发愁的时候,只见老村长拿起一根棍子,在一片空旷的沙地上画了一个很大的“场地”,并且在“场地”里画了演出舞台、入场处。令人既吃惊又感动的是,演出开始以后,人们发现大人小孩凡是买了票的,都整整齐齐地有的拿着小板凳、有的席地而坐在圆圈里,没有买票的则规规矩矩地站在圆圈外边,没有一人越过画在沙地上的线。文工团有人感动地一再喊话让圆圈外的村民站到圆圈里边来,然而,嗓子喊哑了也没有一个人进来,大家一直守规矩地看完最后一个节目。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发现前一天晚上的圆圈竟然还清晰可见,许多演员激动地掉了眼泪。“圆圈”故事真实地再现了迪坎尔村民的纯朴和善良,同时也反映了迪坎尔村的落后和村民的封闭、保守,甚至愚昧。当时的鄯善县县委书记郭庆泰和组织部长何立新在这里蹲点,主要想通过基层组织建设,强化村级班子,引导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解放思想,打开封闭之门。他们动员县里乡里的机关干部和村里的党员干部修路补桥,在村里建起一个农贸市场,本来是想让村民到市场里做生意,然而,市场建成以后竟然没有一个村民来,工作队便动员当时的县供销社送货下乡、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把家里的蔬菜水果、葡萄干和毛驴车缰绳等土特产拿到市场里销售,逐渐引导和带动村民转变观念。后来,我写了一篇《打开封闭之门》发表在《新疆日报》上,当年还获了奖,《新疆经济报》的龚怀山采写了一篇长篇通讯《堡垒是这样铸成的》,真实地反映了迪坎尔村当时的情况。
由于那时还没有人开始探寻或者公开反映迪坎尔人与古楼兰人及罗布泊荒原的联系。今天想来,村民的那种因自我封闭而纯朴的近乎原始的生活态度和对新生事物的认识和接纳,与他们长期居住在罗布泊荒原和不断因生存环境而迁途积淀的习俗、性格等可能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可能与古楼兰人的血统也有直接关系。
而如今,穿村而过的沥青公路一直铺设到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牌子下面,那是村庄的尽头。沿着沥青公路两边盖起了整体的红砖房,祖祖辈辈不习惯做生意的村民开始在公路两旁的家门口开起了小卖铺,而且家家户户购买了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等过去在他们看来几乎想都不敢想的电子产品,村民使用手机的也越来越多,甚至有的人家还看上了数字电视,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其实,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永远是公平的。祖祖辈辈生活在迪坎尔绿洲的古楼兰人后裔似乎没有想到,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罗布泊荒原库鲁克塔格山中蕴藏的丰富矿藏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财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已经探明吐鲁番盆地90%的矿产资源分布在鄯善迪坎乡以南的库鲁克塔格山区,丰富的金、铜、铁等矿藏吸引大批客商投资就地建厂,给1.725万平方公里占地面积中的80%为戈壁荒漠和山区的迪坎尔带来了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据了解,目前已有9家国内企业在昔日的戈壁荒滩投资建厂,其中一千万元以上的企业就有5家,成为新疆重要的矿业基地。企业进村受益最多的理应是进入罗布泊库鲁克塔格山区必经之地的迪坎尔村这些古楼兰人后裔。迪坎尔乡党委书记秦克良说:“罗布泊山区矿产资源的开发,受益最多的当地的老百姓,全乡解决当地富裕劳动力一千多名,其中老迪坎尔(迪坎尔村)占了70%多。”。迪坎尔村老支书玉山·阿不都则自豪地说:“迪坎尔村有257户人家1200多口人,2007年人均纯收入达到3100多元,今年超过1500元应该没有问题,这是10多年前迪坎尔人想都不感想的现实!”
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迪坎尔村的巨大变化,带给迪坎尔这些古楼兰人后裔的是巨大的财富和根本性的观念转变、思想解放,封闭多年的大门终于大开。160多名大学生的诞生和村里悄然兴起的汉语热、打工热、经商热,足以说明迪坎尔村这些经历过无数次不断迁途而定居下来古楼兰人后裔今天的生活是多么幸福!
“楼兰姑娘辫子长长/楼兰姑娘眼泪汪汪/千年幽梦随风去/不知家乡在何方;楼兰姑娘眉毛长长/楼兰姑娘青春飞扬/千年相思腮边挂/不知情郎在何方;/楼兰姑娘乡思长长/楼兰姑娘去向何方/请你尝尝哈密瓜/鄯善就是你家乡……”这是《楼兰姑娘思故乡》的完整歌词,诣在告诉人们,古楼兰文明并没有消亡,古楼兰人并没有灭绝,他们的后裔幸福地生活在哈密瓜的故乡鄯善。
然而,透过探寻古楼兰人后裔,我们清醒地明白了当年在古丝绸之路上辉煌的楼兰古国的消亡缘由,以及古楼兰人因水和大自然的惩罚而长达上千年不断迁徒的逐水草而居的颠沛流离生活,启迪今天的人们更加珍惜和热爱我们的家园、建设我们的家园,不再重蹈古楼兰消亡的覆辙……
罗布泊历经岁月沧桑,到公元1975年夏天被太阳蒸干了最后一滴水。曾经烟波浩淼数千年,滋养了古楼兰文明的罗布泊,终于变成了茫茫沙海。
在罗布泊渐渐干枯的过程中,楼兰古国的臣民们相继搬迁到了哪里呢?他们今天生活的怎么样?
我虽然不是一名史学家,但作为一种对历史和事物的好奇,多年来我一直注意收集有关资料,曾经沿着史料的路径,多次到进入罗布泊荒原的吐鲁番盆地最南端的鄯善县迪坎尔乡迪坎尔村和南疆的尉犁县进行过寻访。
2008年7月初,我参加了吐鲁番地区作家协会组织的“关注楼兰最后一个村落――迪坎尔”活动,有机会再次近距离了解这个在地缘、民族、文化传承和血缘上与神秘消失了的楼兰古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的古老村落,以及生存在这个古老村落里的那些古朴、善良的与古楼兰人一脉相连的人们从罗布泊荒原迁途的故事和他们的现实生活。
走进盆地边缘的迪坎尔绿洲
七月流火。如果说吐鲁番盆地是“火洲”,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挟裹在著名的库木塔格沙漠和罗布泊荒漠之间的盆地边缘的迪坎尔绿洲就是名副其实的“火炉”。库木塔格沙漠由来至东天山七角井风口和西天山达坂城风口的两股强烈气流,所挟带的大量沙子在库木塔格山地相遇撞击沉积而形成,处在吐鲁番盆地最南端,而罗布泊荒漠则是众所周知的戈壁瀚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造就了迪坎尔绿洲“特殊”的神秘,以及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绿洲里的250多户“特殊”的村民。
迪坎尔绿洲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是一个被沙漠裹挟的村庄,柏油公路通到这里就停止了,一条连接文明与蛮荒的路也到此为止,绿洲也到此戛然而止,就好像这里已是大地的尽头、人类生存的边缘。它的东边是库木塔格沙漠铁色的沙山;向南是罗布泊无边瀚海;西边的流沙一年四季拍打着脆弱的绿洲;北边虽与绿洲相连,但可以看到流沙一直想把它撕开,使其成为一个孤岛,以图最终把它淹没。村庄就在公路的两边,村民的屋后就是库木塔格沙漠和罗布泊荒原的戈壁滩,无情的风把村民屋后的戈壁沙漠雕凿成一幅幅千奇百怪的巨型图案,迪坎尔绿洲则像戈壁沙海中的一个绿色孤岛、一叶泛舟……不管从村里的公路上穿过的是什么,也不管村里来了什么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庄依然保留着原始而古老的朴素,村民们依然保持着纯朴而随遇而安的祥和、安逸的似乎完全与他们生活的这片绿洲融为一体的生活方式。绿洲之所以世代枝繁叶茂、村民们之所以自由自在地繁衍生息,一切缘于村里那22条至今常年流淌的坎儿井和村民对水的珍惜、对生活的知足感。村民至今仍然沿袭着“先掏挖坎儿井,架起辘轳再成家”的习俗,姑娘嫁人首先要打听小伙子家附近有没有坎儿井和辘轳,吃水方不方便?小伙子要成家最要紧的是要学会掏挖坎儿井技术,否则会一辈子打光棍。难怪穿村而过的那条一年四季都清澈如镜的温泉坎儿井流淌的那么畅快(据说,温泉坎儿井冬季最冷时的温度在35摄氏度左右。)!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一架古老的木质辘轳,以至于迪坎尔村现在的一些自然村仍然以掏挖坎儿井的人和掏挖坎儿井的村子命名坎儿井,比如:米里克阿吉坎、牙克甫坎、纳瓦依坎(纳瓦依村)等等。
生活在迪坎尔村的村民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们与神秘的古楼兰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令人惊叹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生活追求。迪坎尔人对事物的理解有着他们自己的特殊方式,坎儿井是谁掏挖的就用谁的名字命名,哪个自然村什么东西出名、特殊就用什么命名,形成了现在一直在沿用的纳瓦依村(打馕人的村子)、其可其村(裁缝村)、牙克坎来苏(最边上的村庄)等自然村。迪坎尔村的很多人熟悉罗布泊就像熟悉自己家的院子和地里的葡萄瓜果、棉花和圈里的羊群一样,他们对罗布泊的地里环境和风沙、风向十分熟悉,村里的大多数人至今还经常到罗布泊荒漠里放牧羊群和骆驼。在这里,许多与现代文明看似格格不入、蒙着一层神秘面纱的现象,以及村民将古朴生活自然沿袭又自然而然地不断接纳现代生活的生存方式,一些偶尔遇见的黄头发、蓝眼睛村民和至今仍然居住在100多年以前用生土建造的土屋里而冰箱、彩电、甚至数字电视、电脑等现代生活品一应俱全的现实生活,让人的心灵不断受到强烈的抨击。更加令人惊叹的是,在这样一个边缘、荒凉的戈壁沙漠包裹下的村庄里,人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对学习汉话的热情、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尤其是对国家大事的了解和理解,如果不是身处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你很难想像到他们是生存在迪坎尔绿洲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的农民!
我大胆地设想:迪坎尔绿洲人们的这些“特殊”是不是古楼兰人血脉和生活习俗的延续?!
我们这些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走在热浪滚滚的迪坎尔村的村道上,走进百年古村那“冬暖夏凉”的生土建造的土屋,与始终面带纯朴的微笑、偶尔遇见的黄头发、蓝眼睛的村民搭话、聊天,吃住在他们的家里,与他们面对面接触、沟通,感受他们千百年来几乎一成不变的知足、安逸、和谐、纯朴而安然的生活。尽管从早到晚都有一种生活在“桑拿房”里的不适,但是,他们那近乎古朴的憨厚和友好,以及对我们这些外来人始终“不设防”的诚实和信任,还有那些老人和孩子善良、友好的眼神……这些始终令我的灵魂震颤、意识神游、飘逸、动荡的现实,使我有一种在楼兰古国里畅游的神往。
记得刚到迪坎尔那天晚上,由于天气实在太闷热,我和地区作家协会的刘秘书长,还有鄯善县文联的一名作家在“罗布泊向导”白克力·艾海提的安排下,住在他家屋后的迪坎尔烽火台宽大、平坦的台面上。在漫天繁星下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的烽火台上,我们三个人一边畅想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和罗布泊荒漠中古楼兰的美丽、繁华,以及楼兰美女的风姿卓韵、千娇百态,一边神侃千古奇闻、古今文人墨客对楼兰古国、楼兰美女的向往和赞叹。不知不觉中我们干掉了两瓶东北老酒,眼前的镜像顺着意境开始像梦游一样在自己的意识里游走、幻想……我对躺在我旁边的刘秘书长神侃眼前的幻影。仰望头顶正对的北斗七星勺把和数也数不清的繁星以及繁星下空旷的银灰色库木塔格沙漠在不远处的迪坎村道上穿梭的车灯折射下映射出的酷似古城墙的影像,不知道是潜意识的驱使还是大自然的神奇幻影,我告诉刘秘书长我看到了楼兰故城高高的城墙和城墙上楼兰美女的婀娜舞姿、城墙下热闹繁华的市井、车马……
尽管酒后夜宿迪坎尔烽火台我看到是一种自我意识神游的幻影,但是,黎明前站在迪坎尔烽火台上、站在库木塔格沙漠的沙山顶上,遥望远处库鲁克塔格山脉银灰色山峦起伏绵延周围的罗布泊荒漠的凄美和库木塔格沙漠与罗布泊荒漠之间的迪坎尔生机盎然的绿洲,我似乎感觉到自己终于触摸到了古楼兰人迁移的些许脉络,以及迪坎尔绿洲与楼兰古国的密切联系和迪坎尔人与楼兰人之间存在的神秘渊源。
探寻古楼兰人后裔迁途踪影
据史料记载,楼兰古国,原位于鄯善县南部的华夏第一县若羌县北、神秘的罗布泊以西、塔里木盆地东缘,迄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被中外学者誉为沙漠中的“博物馆”、“东方的庞贝城”。《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捍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四万四千一百。”
“地名搬家”是历史上地名常见的一种现象,一般同人口迁徙相联系,今天的“鄯善”县名就源自鄯善人的迁徙。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西汉王朝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派平乐监傅介子刺杀了位于塔里木盆地东缘亲匈奴的楼兰国国王,另立新王,并将楼兰国名改为鄯善。此后数百年间,鄯善一直是楼兰的国家名称。我们今天所说的楼兰,实际上是鄯善国的一座重要城市。当时这里是塔里木盆地重要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5~6世纪时鄯善国屡遭攻击,多次被灭,从而造成鄯善人口多次向外逃徙,相毗邻的高昌成了鄯善居民逃难避祸的场所。公元5世纪末,南齐使者江景玄受命出访西域,当他到达鄯善(楼兰)时,发现这个富庶的绿洲王国已经被丁零人消灭了,百姓们都已四处逃散,整座城池空无一人。此后的1500年间,再也没有听到过楼兰的消息,这个曾经声名远扬的古国如一阵风消失在浩瀚的沙漠戈壁里。1901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意外发现楼兰的消息轰动了世界。与此同时,诸多谜团也随之摆在人们面前:楼兰是怎么灭亡的?楼兰人是什么民族?其语言、文字、风俗又是怎样的?国家灭亡后,楼兰人去了哪里?
许多史料证实,最后的楼兰人后裔(罗布人)迁出罗布泊地区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60年代。也就是说,楼兰古国在公元三世纪神秘消失以后,楼兰古国的臣民们并没有全部逃散、迁走,他们固守在罗布泊,逐水而居,直至水一滴滴蒸发而迫使他们不得不继续迁徙。楼兰人的迁移时空跨度延续了大约1700多年,他们的主要迁往地有南疆地区的若羌、且末、尉犁和东疆地区的鄯善、哈密、伊吾,以及内地的青海、甘肃、西安、河南等地,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最后一批楼兰人的后裔才从罗布泊荒原的辛格尔迁到了今天鄯善县的迪坎尔村。
《魏书.鄯善传》、《宋书.索虏传》等史籍中记载:公元422年,鄯善王比龙世子率4000余国民归降北凉王沮渠安周,并随其迁居高昌。来到高昌后,这部分楼兰人被安置在库姆塔格沙漠北缘的绿洲地带,楼兰人将这片绿洲命名为“蒲昌”,以示对故乡罗布泊蒲昌海的纪念。至今,当地维吾尔族群众仍将鄯善称为“辟展”,即“蒲昌”。有关专家也认为,今天的鄯善县东巴扎故城遗址其实就是唐代的蒲昌城遗址。楼兰人向吐鲁番盆地的移民活动也被在火焰山下的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代文书所证实,这些文书中记载了大量关于“鄯”、“善”姓人名,考古学家根据西域人以国为氏的习惯,断定这些人都是楼兰国的移民。
走近迪坎尔绿洲古楼兰人后裔
古老的楼兰王国虽然消亡了,但它的臣民们在迁往新的栖生之地以后,在古老的罗布荒原周边的绿洲,又建立起了新的幸福、祥和的家园,创造了西域古老的历史文化、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楼兰文明也因此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延续。
约翰·海尔在他1998年出版的中文版《迷失的骆驼》一书中,详细记录了他深入罗布泊腹地探险、寻访野骆驼的经历。这个英国人在他的著作里清楚地记录下了最后迁移的楼兰人后裔,他们于20世纪60年代迁到了今天鄯善县的迪坎村。约翰·海尔在他的著作中记述了迪坎尔村的楼兰人后裔吐尔迪阿訇,他爷爷的哥哥阿不都热依木就是1901年与罗布人奥尔得克一起为斯文·赫定做向导的罗布泊猎人。斯文·赫定在《我的探险生涯》中描述:“在都拉里村北的一个树林里,我们巧遇从北面辛格尔来的阿不都热依木,他是整个沙漠中仅有的两三个知道‘六十个泉’的猎人之一……解决那个移动的罗布淖尔的问题,要经过沙漠没有一个起点比‘六十个泉’更稳妥,我决定雇佣他和他的骆驼。”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水,是罗布淖尔(罗布泊)的灵魂所在,没有了它,罗布淖尔(罗布泊)便成了没有生命气息的荒原。楼兰人,也是这样一点点散失了自己的家园,并且,永无返还的可能,最终使曾经在丝绸之路上十分辉煌的楼兰王国消失在罗布泊荒原中。
罗布人奥尔德克1934年又再次帮助另一个瑞典人贝格曼(有人说是斯文·赫定的助手)发现了罗布泊荒原中著名的小河(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小河墓地),发现一具保存完好的“楼兰美女”船形棺木,被其安祥的神情和完好的保存所震惊,称她为“楼兰公主”,但他无法带走她,只好就地掩埋。“楼兰美女”中有两个非常著名,一个是1980年发现的楼兰美女,那是在我国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楼兰科考时,于龙城雅丹南边一带发现的女干尸,当时轰动一时,这位楼兰美女生活于公元前3900年左右,有棕黄色的头发,皮肤呈红棕色,后来被新疆博物馆收藏。另一个是2004年小河遗址重新被发现后,在那里出土的一具女干尸,她比1980年的那具保存得更完整,并且更加年轻美丽。1980年的那具是壮年妇女,有40岁左右;而这具只有20多岁,身材更修长,长相也非常清楚,这具名副其实的楼兰美女被收藏在若羌博物馆。后来专家将两位楼兰美女头像复原,供更多的专家考证。通过躺在博物馆里“楼兰美女”和专家复原了楼兰美女画像,我们似乎觉得古人和今人的距离并不是那么遥远。
新疆青年诗人沈苇说:“奥尔德克既是出色的向导,更是沙漠里的预言家。一位土著居民不自觉地发现与职业探险家自觉地发现结合起来,才使我们对历史的挖掘、对文明的探寻成为可能。”。
奥尔德克的后人后来迁移到了罗布泊荒原的辛格尔居住,60年代初迁到了迪坎尔村。他的孙子白克力·艾海提如今成了著名的“罗布泊向导”,经常带领国内外的探险家出入罗布泊荒原,似乎在有意无意间巧妙地步入先辈的后尘。其实这是一种无法言表的血脉传承,所不同的只是时代和环境、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罢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人约翰·海尔和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专家袁国映教授、探险家赵子允一起,考察过面临灭绝的野骆驼的生存状况,之后写了著名的《迷失的骆驼》,书中有一张迪坎尔村吐尔迪阿訇的照片。去年8月中旬,我踏着流火的热浪,在迪坎尔村支部书记玉山·阿不都的引领下,找到了约翰·海尔在著作中提及的罗布人后裔吐尔迪阿訇的家。
吐尔迪阿訇现在的名字叫叶赫亚·沙依木。改名字的事情还有一段故事。被称为新疆“麦加”的吐峪沟清真寺依玛木觉得他原来的名字没有什么意义,于是在1986年春天的一天便给他改为现在的名字,意为“永远不老,健康长寿”。提起《迷失的骆驼》一书中关于他的一张照片,已经70多岁的叶赫亚·沙依木显得很兴奋,他说这是“骆驼子”(他对约翰·海尔的昵称)1997年春季来迪坎尔时照的,当时自己57岁。他告诉我,他们一家是1950年春天才从罗布泊荒漠的辛格尔迁到吐峪沟乡洋海村的,1956年又从洋海村搬到辛格尔生活了5年,1960年春天又迁到了当时水草丰茂的迪坎尔村。叶赫亚·沙依木说,他们一家在罗布泊荒漠的辛格尔生活了好几代人,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了。据老人们讲,从鲁克沁王时代他们就生活在辛格尔,因为那里水草茂盛,野生动物很多,是大家生活、狩猎的好地方。那时候居住在辛格尔的人有很多家,老辈人能够记住的大概有好几十家人,祖祖辈辈居住了有一百三四十年了,他自己是家族中的第四代,就出生在辛格尔。
老人肯定地说:“我的家族很久以前是生活在鄯善的,我家是鄯善人。”接着又他有补充说:“我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罗布淖尔(罗布泊)边上的鄯善。”
其实,老人所说的“鄯善”就是当年罗布泊荒原中的楼兰王国。约翰·海尔在《迷失的骆驼》一书中只写下了“可能是罗布人后裔”等文字,也许是因为他没有搞清楚“楼兰”、“罗布泊”、“鄯善”之间的关系的缘故。考古专家在鄯善县境内挖掘出土的文书中,陆续发现了近60个姓“鄯”和“善”的人,文书纪录了他们在鄯善生产、生活的历史,证实了最后一批楼兰人中的一部分人在这里驻足停留、生活,并最终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见到叶赫亚·沙依木老人,不得不提奥尔德克这个名字。叶赫亚·沙依木老人兴奋地说:“罗布人奥尔得克和我爷爷的哥哥阿不都热依木经常在罗布淖尔(罗布泊)打猎,以后他们一起给外国人管骆驼,做向导。”他说,奥尔德克的祖先也是老鄯善人(楼兰国人),也生活在罗布淖尔(罗布泊)。大概是1901年的四五月份,有几名外国人(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等人)找到奥尔德克,要找一批当地人给他们驮运物品,带他们进罗布淖尔(即罗布泊)测量(实际是探险考古)。奥尔德克从阿布达勒村赶到辛格尔找到我家,让我爷爷的哥哥阿不都热依木和他一同去。
至于叶赫亚·沙依木和迪坎尔绿洲的村民是什么时候从罗布泊迁到辛格尔,以后又为什么从辛格尔迁到了迪坎尔绿洲的?迪坎尔人的说话比较一致。老人和村里其他从辛格尔过来的村民介绍,大概是一百二十多年前,罗布淖尔(罗布泊)的水越来越少,住在那里的最后十几户人家都搬走了,有的搬到了且末,有的搬到了尉梨,有的搬到了其它地方,他的祖爷爷和另一家人搬到了距罗布淖尔(现在的罗布泊湖心)西北150多公里的辛格尔。因为辛格尔在库鲁克塔格山北,那里有辛格尔布拉克(辛格尔泉)、依尔托古什布拉克(依尔托古什泉)等六十六个大大小小的泉,还有碧绿的草场、肥沃的土质。在辛格尔,他们生活了大概四代人。大概到了60年代初,新疆马兰基地部队进驻罗布泊周围,国家搞原子弹实验,辛格尔人就陆续整体搬迁了出来。叶赫亚·沙依木家和他家住在一起的另一家搬到了尉梨县的一个偏远的地方,后来又搬到了尉梨县附近的胡杨林(现在的尉犁县罗布人村寨风景区附近)。叶赫亚·沙依木一家搬到了现住的迪坎尔村。由于叶赫亚·沙依木的父亲认为他们是鄯善人,鄯善都迁到吐鲁番的辟展了,他们也应该去鄯善,所以父亲带着他和弟弟迁到了今天的迪坎尔村。叶赫亚·沙依木告诉我,他们在这里一直生活的很好,很幸福。
别看只有50多岁的玉山·阿不都其貌不扬,平时不善言谈,可他已经在迪坎尔村当了14年的村支书了。他介绍说,迪坎尔村现在全是土生土长的维吾尔族人,很多人都是从外地迁来的。由于各种原因,从罗布泊荒原的辛格尔搬迁到迪坎尔村的人家到底有多少很难说清楚,现在能够有记忆的大概也就几户人家,比较出名一些的也就是叶赫亚·沙依木一家和艾海提·米里克一家。因为,叶赫亚·沙依木爷爷的哥哥阿不都热依木曾经带外国人(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等人)发现了罗布泊里的楼兰古城遗址,以后经常有外国人和许多专家、旅游的人,还有新闻记者等来找他们家了解情况,名气比较大一些。艾海提·米里克父亲的哥哥就是和叶赫亚·沙依木爷爷的哥哥阿不都热依木带领外国人发现古楼兰遗址的阿不都米力克·奥尔德克,不过很少有人提起过,因为时间太长了,很多事情没有人能够记得那么清楚,他们家出名是因为他的儿子白克力·艾海提。提到白克力·艾海提,玉山·阿不都书记眼睛里充满了神采,他说:“白克力这个人是迪坎尔村现在很有威望的人,他经常带领外国人去罗布泊,继承了祖辈的血脉。艾海提·米里克一家是60年代初才从辛格尔搬迁到迪坎尔村的,可能是最晚从辛格尔搬迁来的。”。我问他:“你们的祖辈人是不是也是从罗布泊的辛格尔搬迁来的?”他憨厚地笑着说:“搞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们家是多年以前从鲁克沁搬到迪坎尔村的。”
其实,与从辛格尔搬迁到迪坎尔村的其他人家一样,无论是叶赫亚·沙依木一家也好,还是艾海提·米里克一家也好,他们在辛格尔都过着半耕半牧的生活。叶赫亚·沙依木一家当时种有10亩地,主要收获的是麦子、大豆、甜瓜等,还养了二三十只羊,冬季就到罗布泊去打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这使我想起了清代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罗布泊人不食五谷、不牧牲畜,以小舟捕鱼为食。”的说法似乎有很大的出入。其实有关专家认为,罗布泊人比印第安人更完整地保留了原始生活方式,几千年前的卡盆(独木舟)和烤鱼的柽柳枝,如今被他们的后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们仍然饶有兴致地使用着。在沙漠里,他们辨别方向的能力胜过罗盘。
叶赫亚·沙依木的母亲、姐姐都去世安葬在了辛格尔,搬迁到迪坎尔村时,他家只有他和父亲、弟弟三个人了。每次想到这段经历时,叶赫亚·沙依木老人都显得有些伤感和沉重。
玉山·阿不都书记领着我去艾海提·米里克家时,已经80多岁的老人坐在木炕上,脸上总是洋溢着慈善、和蔼的笑容,说话、记忆都有一些障碍,无法沟通。老人的孙媳妇告诉我,他的儿子白克力·米里克带领一个探险队去罗布泊了,大概三天以后才能回来。玉山·阿不都书记看到我在夏日酷暑下的失望表情,告诉我,迪坎尔村有一位116岁的老人买合托木汗·吾塔力甫,她是见证栖息在迪坎尔的古楼兰人后裔生活和迪坎尔历史的“活化石”,只是年龄太大,许多事情已经记不清楚了。我知道,迪坎尔村人的生存环境并不好,但村子里长寿的老人却很多。在我的执意要求下,玉山·阿不都书记带我见到了这位老人。老人虽然年事已高,而且无法与人交流,但是看得出身体状况比较好,据家里人讲,她一天三顿饭一直都很正常,而且半年前还能下地走路。在我和她的大儿子司马义·甫拉提简短的交谈交谈过程中,老人一直在用“菩萨”一样的眼神和我们交流着,这让我心中生出一些敬仰和敬畏,好像老人的眼睛能够看穿你的灵魂一样。老人五世同堂,有子孙30多人,她一生养育了15个子女,成活了5个,老大(实际为老三)司马义·甫拉提已经75岁了,身体比较硬朗。据司马义·甫拉提老人和老伴、儿子介绍,他们一家50年代从辛格尔搬迁到尉犁,在那里生活了5年多。因为辛格尔有几十亩地和几十只羊,父亲一直在那里,所以,60年代又搬迁到了辛格尔。以后由于部队在辛格尔驻扎,一家人和邻居一起搬迁到了鄯善县的吐峪沟洋海,一直到60年度末才搬迁到迪坎尔村的。遗憾的是,买合托木汗·吾塔力甫老人2008年4月份不幸仙逝了。7月份再次见到迪坎尔村支部书记玉山·阿不都时,他告诉我,迪坎尔村以前的4位百岁老人都相继去世了,现在村里9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7个。
迪坎尔人与南疆尉犁、若羌,甚至北疆的吉木萨等地一直有着通婚的历史。百岁老人买合托木汗·吾塔力甫娘家就是尉犁人,她的儿子司马义·甫拉提的老伴和儿子、孙子媳妇都是尉犁人,可以看出,他们与尉犁有着很深的血脉联系。
事隔一年以后我再次见到老支书玉山·阿不都时,他还是满脸挂着友善的笑,把外面径直领到了“罗布泊向导”白克力·米里克刚刚盖好的红砖房里,安排我们吃住在他家里。
一见到高大魁梧、一脸憨厚中透露着刚毅的白克力·米里克,我放开目光肆意地在他身上搜寻他的父辈烙下的罗布人或者楼兰人的影子,直到他憨厚地笑着用流利的汉话和我交谈。我说:“很多年以前就知道你了,去年夏天我专门找过你。”他像老朋友一样憨笑着说:“看来我们是有缘人,因为有缘人总会见到的。”。他那憨厚的笑和不怯生的友善也许是因为见多识广练就的,但他从骨子里流露出来的那种友善和憨态,似乎与迪坎尔村的村民如出一辙。
白克力这个名字我还是从北京画院陈雅丹写的文章中和一些断断续续的网络上了解的。其实,人们称白克力是罗布泊“活地图”并不为过,因为,迄今为止,他已经带领300多人进出罗布荒原三十多次。
罗布泊的神秘诱惑着勇敢者,不仅是探险家考古学者的天堂,也日趋成为探险越野爱好者的神往之地,但同时罗布荒原的险恶地形又使太多的人望而却步,若无向导带路,无越野交通工具,无充分的给养,进入罗布荒原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迪坎尔村许多村民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外探险家和考古学者的向导。也许是因为有着正宗罗布人血统的原因,白克力成了村里最有名望的向导。白克力虽然出生在罗布泊荒原的辛格尔,从小也知道人们说的罗布泊荒原中的六十六个泉,但他对罗布泊并没有什么概念,他不太清楚那么多人经常冒险进入罗布泊去做什么,但探险队员们谈起罗布泊时的兴奋和神秘激起了他的好奇。直到2001年8月29日,已故新疆探险家赵子允再一次带队进罗布泊的时候,白克力终于试探着向赵子允提出,想跟考察队进一次罗布泊,看看他们在罗布泊究竟做什么。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已故的新疆探险家赵子允经常带队进入罗布泊考察,每一次出发前和回来后,几乎都在白克力家落脚吃住。这是因为白克力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精通汉语的维吾尔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白克力的爷爷阿不都米力克·奥尔德克和他爷爷的哥哥阿不都热依木曾给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带过路,算是“名人”之后,那些寻踪觅古的人们,对这个颇感兴趣。
白克力·米里克是名副其实的罗布人后裔,家族中共有四代人曾经住在罗布荒原的辛格尔,他们在那里种地、放牧、打猎。现在,先辈的麻扎(墓地)还在那里。后来,爷爷那代弟兄4人中,两家迁到了南疆的尉犁县,两家迁到了现在的迪坎尔村。出于故土难离和对祖先崇拜的情结,白克力的爸爸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每年的春天都带着他,赶着毛驴车,经过3天的长途跋涉,到先辈的拱巴斯(祖坟)朝拜一次。累了,他们就原地休息,在周围转转。渐渐地,他对那里的地形就比较熟悉了,更主要的是他的父亲曾经神秘地告诉了罗布泊六十六个泉的位置。掌握了这个天大的秘密,白克力罗布泊里的一匹“野骆驼”,他曾经开着东风车敢带着乌鲁木齐16名探险人员乘坐一辆轿子车进入罗布泊。那是他第一次带探险人员,经历了6天6夜的生死磨难,最后把全部人员安全带出了罗布泊荒漠。事后他后怕了好长时间,也遭到父亲的严厉批评,很长时间不让他进入罗布泊。赵子允那次带白克力参加探险队事先征得了他父亲艾海提·米里克的同意。白克力负责帮探险队员做饭,沿途哪里有泉水和植物,他都十分熟悉,给赵子允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多次带他去罗布泊当向导。之后,白克力开始了他的职业向导生涯。2003年,白克力为广州游客王灿等七八个人带路,因不适应罗布泊多变的气候和不规律的饮食,王灿患上了肠胃炎,又拉又吐,面色苍白,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一路上,白克力不离左右,问寒问暖,搀扶他上下车,为他打饭。王灿非常感动,走到敦煌时,硬是塞给他1000元作为酬金。白克力用生硬的汉话说:“朋友的事情,还要计较钱不钱的吗?”王灿说:“钱不收吗,朋友不认了!”白克力只得收下。如今,每年的春节,白克力都要把自家产的葡萄干和红枣寄往广州。王灿还专门邀请白克力到广州等地去过,使他打开眼界,更加坚定了自己当罗布泊向导的信心。
“看,这是美国朋友寄来的。”白克力有点炫耀地拿出一个黑色檀香木做的上面雕刻着“华藏山社”和白克力名字的小牌牌和一张他女儿和儿子的照片展示给我们。看到我们分享他的快乐,他又进入房间换上一件印有“华藏山社”字样的黑色体恤衫和一摞照片展示给我们。他特意翻出一张有陈雅丹的照片自豪地对我们讲:“这个,陈宗器的女儿陈雅丹。陈宗器知道吗?他是科学家呢,他以前和斯文·赫定一起进楼兰探险考古。陈雅丹进了罗布泊好几次,都是我带的路,她在罗布泊湖心立的纪念她父亲的碑还是我帮忙立的呢。”他指着照片上的碑给我们看。
白克力不但是一个勇敢而又细心的罗布泊向导和迪坎尔村民羡慕的好人,而且还是一位十分有经济头脑的“商人”。他自己掏一万多元在罗布泊湖心立了三个石碑,分别纪念已故的余纯顺、赵子允和美国探险家朋友,目的是吸引更多的探险家和游人去罗布泊。
看到白克力十分开心地、不厌其烦地拿出照片和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物件向感兴趣的人们介绍,我便在一旁不停地按动快门,记录下这个罗布人后裔今天幸福生活的精彩瞬间。
迪坎尔绿洲古楼兰后裔的幸福生活
公元四世纪起,关于楼兰古国的记载突然从历史消失,不再现于任何史书。它消失的原因,一直是近代中外考古探险家孜孜探寻的谜,以至于对古楼兰人的去向众说纷纭。
历史毕竟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真相。我认为,既然是历史就需要有人书写,而书写历史、挖掘历史的人则是有心者和对历史、对生活虔诚的人。吐鲁番地区作家协会组织当地部分自治区级作家协会会员和对历史、文化、文学有一定兴趣的作者,在流火的七月深入吐鲁番盆地最南端的迪坎尔村,通过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和对他们生存环境的亲身感受,探寻古楼兰人后裔的迁途和他们今天的现实生活状况,这无疑是续写今天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迪坎尔古楼兰人后裔历史的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
今天的人们知道,罕见的蒸发量和几乎为零的降水量,使罗布泊成为真正的“死亡之海”,著名的旅行家,人称当代徐霞客的余纯顺,著名科学家彭加木都魂断这里。然而岁月如烟云散去,万古沧桑却留遗痕,人们共同的感受是:绝域罗布泊,依然充满荒凉可怖,凶险神秘。楼兰古国尽管离我们已经远去2000多年,留给我们的仅仅是一个遥远的神秘背影,然而,苍天有眼,他的臣民们却凭着顽强的生命力,一代代沿着历史的轨道向我们走来,通过寻访和史料佐证,古楼兰人的后裔们(古鄯善人)依然和今天的鄯善紧密联系在一起,难怪清光绪28年(1902年)辟展建县时定名“鄯善”,这说明当时的清王朝官员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有一部分古楼兰人(古鄯善人)的后裔逐水草而居,早已翻过库鲁塔格山北迁到了今日的鄯善。
我想,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一味地去探讨、考证一些历史史料的准确性,而应该把目光放在现在依然生活在罗布泊和库木塔格沙漠之间的迪坎尔绿洲的这些古楼兰人后裔的现实生活上,续写古楼兰人新的历史篇章,让更多的人了解古楼兰人后裔在现代社会中不再逐水草而居的幸福生活。
对于迪坎尔村我并不陌生,对于迪坎尔村今天的巨大变化我由衷感到欣慰!
1992年的冬天,我曾经采访住村的鄯善县工作队时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和柏油路,村民过着近乎原始的生活,日常生活基本采取的是“易货交易”,也就是说以东西换自己需要的东西,就连吃的盐巴也是赶着毛驴车从罗布泊的盐山拉运,自给自足,过着清静而与世隔绝的封闭生活。村里的老辈人讲,整个村庄几乎没有一个人去过只有80多公里的鄯善县巴扎(集市),更不用说100多公里的吐鲁番了,唯一见识过巴扎的是村里的老阿訇。那是新疆解放以后的一年春季,听说鲁克沁王居住的地方成了穷人随便走动的地方,村民便请求老阿訇代表全村人去见识一下。我记得在鄯善县当过县委书记的岳立仁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改革开放初期,吐鲁番地区一个文工团来到迪坎尔村有偿演出,没有演出场地,一时难住了工作人员。正在大家发愁的时候,只见老村长拿起一根棍子,在一片空旷的沙地上画了一个很大的“场地”,并且在“场地”里画了演出舞台、入场处。令人既吃惊又感动的是,演出开始以后,人们发现大人小孩凡是买了票的,都整整齐齐地有的拿着小板凳、有的席地而坐在圆圈里,没有买票的则规规矩矩地站在圆圈外边,没有一人越过画在沙地上的线。文工团有人感动地一再喊话让圆圈外的村民站到圆圈里边来,然而,嗓子喊哑了也没有一个人进来,大家一直守规矩地看完最后一个节目。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发现前一天晚上的圆圈竟然还清晰可见,许多演员激动地掉了眼泪。“圆圈”故事真实地再现了迪坎尔村民的纯朴和善良,同时也反映了迪坎尔村的落后和村民的封闭、保守,甚至愚昧。当时的鄯善县县委书记郭庆泰和组织部长何立新在这里蹲点,主要想通过基层组织建设,强化村级班子,引导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解放思想,打开封闭之门。他们动员县里乡里的机关干部和村里的党员干部修路补桥,在村里建起一个农贸市场,本来是想让村民到市场里做生意,然而,市场建成以后竟然没有一个村民来,工作队便动员当时的县供销社送货下乡、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把家里的蔬菜水果、葡萄干和毛驴车缰绳等土特产拿到市场里销售,逐渐引导和带动村民转变观念。后来,我写了一篇《打开封闭之门》发表在《新疆日报》上,当年还获了奖,《新疆经济报》的龚怀山采写了一篇长篇通讯《堡垒是这样铸成的》,真实地反映了迪坎尔村当时的情况。
由于那时还没有人开始探寻或者公开反映迪坎尔人与古楼兰人及罗布泊荒原的联系。今天想来,村民的那种因自我封闭而纯朴的近乎原始的生活态度和对新生事物的认识和接纳,与他们长期居住在罗布泊荒原和不断因生存环境而迁途积淀的习俗、性格等可能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可能与古楼兰人的血统也有直接关系。
而如今,穿村而过的沥青公路一直铺设到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牌子下面,那是村庄的尽头。沿着沥青公路两边盖起了整体的红砖房,祖祖辈辈不习惯做生意的村民开始在公路两旁的家门口开起了小卖铺,而且家家户户购买了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等过去在他们看来几乎想都不敢想的电子产品,村民使用手机的也越来越多,甚至有的人家还看上了数字电视,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其实,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永远是公平的。祖祖辈辈生活在迪坎尔绿洲的古楼兰人后裔似乎没有想到,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罗布泊荒原库鲁克塔格山中蕴藏的丰富矿藏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财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已经探明吐鲁番盆地90%的矿产资源分布在鄯善迪坎乡以南的库鲁克塔格山区,丰富的金、铜、铁等矿藏吸引大批客商投资就地建厂,给1.725万平方公里占地面积中的80%为戈壁荒漠和山区的迪坎尔带来了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据了解,目前已有9家国内企业在昔日的戈壁荒滩投资建厂,其中一千万元以上的企业就有5家,成为新疆重要的矿业基地。企业进村受益最多的理应是进入罗布泊库鲁克塔格山区必经之地的迪坎尔村这些古楼兰人后裔。迪坎尔乡党委书记秦克良说:“罗布泊山区矿产资源的开发,受益最多的当地的老百姓,全乡解决当地富裕劳动力一千多名,其中老迪坎尔(迪坎尔村)占了70%多。”。迪坎尔村老支书玉山·阿不都则自豪地说:“迪坎尔村有257户人家1200多口人,2007年人均纯收入达到3100多元,今年超过1500元应该没有问题,这是10多年前迪坎尔人想都不感想的现实!”
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迪坎尔村的巨大变化,带给迪坎尔这些古楼兰人后裔的是巨大的财富和根本性的观念转变、思想解放,封闭多年的大门终于大开。160多名大学生的诞生和村里悄然兴起的汉语热、打工热、经商热,足以说明迪坎尔村这些经历过无数次不断迁途而定居下来古楼兰人后裔今天的生活是多么幸福!
“楼兰姑娘辫子长长/楼兰姑娘眼泪汪汪/千年幽梦随风去/不知家乡在何方;楼兰姑娘眉毛长长/楼兰姑娘青春飞扬/千年相思腮边挂/不知情郎在何方;/楼兰姑娘乡思长长/楼兰姑娘去向何方/请你尝尝哈密瓜/鄯善就是你家乡……”这是《楼兰姑娘思故乡》的完整歌词,诣在告诉人们,古楼兰文明并没有消亡,古楼兰人并没有灭绝,他们的后裔幸福地生活在哈密瓜的故乡鄯善。
然而,透过探寻古楼兰人后裔,我们清醒地明白了当年在古丝绸之路上辉煌的楼兰古国的消亡缘由,以及古楼兰人因水和大自然的惩罚而长达上千年不断迁徒的逐水草而居的颠沛流离生活,启迪今天的人们更加珍惜和热爱我们的家园、建设我们的家园,不再重蹈古楼兰消亡的覆辙……
参考资料
- 上一篇:一切随缘丨田永庆书画作品欣赏
- 下一篇:赵望进书法艺术展昨日开展
- 古玩赌石鉴宝捡漏类小说,肩关节损伤多久2024-04-25
- 古玩瓷器收藏,梦见家里发洪水是什么意思2024-04-23
- 收购古董古玩,梦见已故同事是什么意思做2024-04-23
- 古玩上门收购,八字教你挑贤妻2024-04-22
- 古玩拍卖出手,左侧颞叶脑出血后遗症2024-04-20
- 古玩拍卖公司,移植后为什么要打肝素2024-04-20
- 深圳有几个古玩城,牙肉红红的是什么原因2024-04-20